【摘自即将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方舟子破解世界之谜》一书。】
《科技日报》2001年9月7日登了一则要闻《萧山老太“自燃”是真是假》,报道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明朗村88岁老太颜文英会“自燃”,据其自述和家人报告,家中家具、衣服经常被烧毁。自从老太“自燃”现象发生后,村干部多次对老人的赡养纠纷进行了调解,取得了满意的结果,就没有再出现过“自燃”现象云云。如郭正谊先生所指出的,这实际上是社会问题,不是科学问题,可能是老太通过装神弄鬼来解决赡养问题,也可能是老太的家人传出“闹鬼”传闻以达到“家丑不外扬”的目的,或想借机把老太太送走。然而,却有两位浙江大学的“人体科学专家”把这当成了科学问题加以解释。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浙江省人体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田维顺称:“这实际上是人体潜在的特殊生理现象。这一现象过去也有报道。……我认为,老妇发火引燃,就是因为她在无周围因素干忧的安静状态时,身体的某些部分的细胞流动趋于同步化,细胞代谢产生了能量的聚集,身体某些部位或全身发热,能量聚集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引燃物体。”浙江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副教授、浙江省人体科学研究会理事毛法根的说法更玄乎:“关于萧山颜文英老太太人体自燃现象,可以从耗散结构和混沌科学来解释。……人消化粮食,在人体内生成葡萄糖。人消化葡萄糖反应称糖酵解,有13个反应步骤。其中有两个步骤是耗散结构振荡。生成成分NADH(即辅酶A)的振荡波。后来发现:这些振荡波的频率,与人的人体信息波的频率重合。这就说明人体内存在由于消化葡萄糖而产生的某种人体信息波。这种人体信息波可以在人体周围形成一种人体信息波场。人体信息波在体内运行过程可以产生能量的积聚。人体信息波在经历无数次迭代之后,突然产生某个窗口,使人体信息波的能量密度增大到多少个几千万倍。这样大的能量可以使人周围的可燃物体燃烧。这就揭开了人体内的人体信息波能量急剧增大的机理。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积聚。只有像颜文英老太太这样极少数人在身体条件极佳时才可能产生。这个迭代所产生的高能,产生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是偶然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它是不确定的。”
这都是典型的伪科学解释。“细胞流动趋于同步化”、“细胞代谢产生了能量的聚集”、“耗散结构振荡”、“人体信息波”云云,都是堆砌杜撰的术语捏造出来的貌似科学而其实不知所云的伪科学说法,如果体内能量能大到他们所说的那样,萧山老太早就没命了。毛法根称“能产生人体自燃现象的人,几百年前就已发现”,其实以前的所谓“人体自燃现象”,并不是像萧山老太这样只点燃东西不烧伤自己,而指的是身体“自己”起火,受害者往往被烧死,甚至烧成了灰。这种说法,的确是几百年来一直有人在主张,也一直有人在驳斥。
1853年,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出版长篇小说《荒凉山庄》,里面有一个名叫克鲁克的邪恶酒徒,最后自燃而死,狄更斯以此象征社会邪恶终将自我毁灭:“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以任何名字称呼这种死亡,将它归咎于某个人,或声称你可以如何避免,但是它一样是永远的死亡--与生俱来的、先天的、由邪恶的身体的腐败体液所自己产生的,并且是唯一的--自燃,而没有任何其他的死亡方式。”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约翰·亨利·列维斯(John
Henry
Lewes)因此批评狄更斯是在宣扬迷信,德国大化学家李比希在同一年也指出:“人能够自燃的说法,并不是建立在死亡因素的知识之上,而是走向知识的反面,建立在对引起事故的所有因素和条件完全无知之上。”狄更斯援引历史上有关人体自燃的记载为自己辩护。他引用的一个例子发生于1725年2月19日法国莱茵,一家客店的女主人米勒太太被发现在厨房火炉旁边烧成灰烬,只剩下部分头颅、下肢和一点脊椎,部分地板也被烧过。她的丈夫被认定谋杀了她,并被判处死刑。上级法院推翻原判,将死因改为“上帝的惩罚”,释放了她的丈夫。狄更斯举的另一个例子发生于1731年4月4日的意大利,一位62岁的公爵夫人被发现身体烧得只剩下部分头颅和四肢,骨灰中有“油腻、发臭的潮湿物”,空中漂浮着烟垢,窗口“滴淌着油腻、令人恶心的黄色液体,发着异常的臭味。”1745年,一位调查者向伦敦王家学会报告这起事故时,也将原因归于人体体内可燃物质在酒精的作用下自燃。其实这两个例子都可以找到外在的火源。在第一个例子中,米勒太太是个天天喝酒的酒棍,她到厨房大概是像往常那样在火炉边喝酒,而她的残骸就倒在火炉边。很可能,她喝醉了以后,衣服着火了。第二例子中,人们发现地板上躺着一盏布满灰烬的空灯,显然公爵夫人弄倒了油灯,并倒在上面而被点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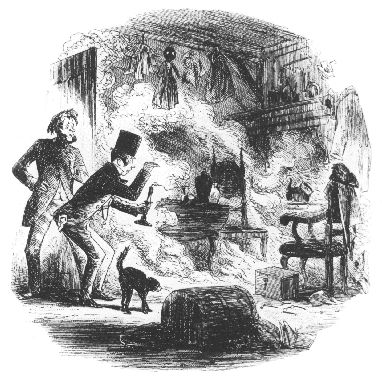
(狄更斯《荒凉山庄》中克鲁克自燃身亡的情景。)
从18世纪至今,大约有四十几起案例被宣称是属于“人体自燃”。事实上,从来没有人亲眼看见人体自燃,这些都是宣扬者根据事后记载的推断,并且有意忽略了可以说明起火原因的重要细节。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发生于1951年7月2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这一天8点,房东卡宾特夫人替67岁的寡妇玛丽·里瑟(Mary
Reeser)签收了一份电报,当她走到里瑟的房间门前时,发现房门的把手滚烫。她大喊“救命”,两名油漆工从街道对面跑过来帮忙,打开门一看,发现房间里热气缭绕,里瑟已被烧成灰烬,只剩一只穿着黑拖鞋的脚和一个“缩得很小的头骨”(可能是颈椎),里瑟所坐的沙发椅也已烧毁,只剩弹簧堆积在灰烬中。调查人员赶来后,注意到天花板和墙壁的上半部被熏黑,墙上塑料插座、浴室里的塑料杯子和衣橱中的蜡烛也融化了。一个电子钟停在4点20分,改插到其他插座后还能走动。调查人员估计里瑟的体重为175磅,被烧得不到10磅,就像是在火葬炉中烧过一样。消息传开后,人们提出了种种解释。有的说里瑟老太太是被人用喷灯谋害的,有的说她是吃了爆炸性物质被炸得粉身碎骨的,也有的说她是被球状闪电击中的。当然,有许多人说她是自燃而死,这个案例因此被宣扬为人体自燃的“有最佳记录的现代案例”。

(调查人员在调查里瑟老太太被烧死的现场。)
这些宣扬者经常忽略了一些能说明问题的重要细节。在前一天晚上8点30分,里瑟的儿子在探亲完毕回家之前,里瑟告诉他她已吃了两粒安眠药,并准备再吃两粒。晚上9点,房东透过窗口看到里瑟老太太穿着由易燃布料制成的睡衣和外套,坐在沙发椅上吸烟。因此,起火的原因并不是那么难以想像的:里瑟在吸烟时睡着了,烟掉到衣服上引起了火灾。
如果我们把这些“人体自燃”的案子放在一起比较,会发现它们具有以下特征:
一、所有案例都发生于室内,并总是致命的。死者总是已独处了很长时间,发现者即使在附近,也从未听到任何惨叫或高喊“救命”的声音。
二、死者大部分是女性,往往身材肥胖,有酗酒恶习,而且死亡经常发生于饮酒之后。
三、死者被焚烧的程度一般要比正常火灾严重,但是身体的焚烧程度并非均匀分布的。四肢通常未烧毁,而躯干被烧的程度最严重,在许多案例中,躯干完全被烧毁,骨头被烧成了灰烬。
四、火势局限于人体和附近,而没有蔓延开去,周围的家具一般未受损或损害不大。
五、尸体、骨灰下面的地板往往覆盖着一层气味难闻的、粘稠的黄色油状液体。
六、焚烧从来不是自发产生的,在死者的周围总可以找到火源,例如油灯、蜡烛、火炉、香烟。另外,有些所谓“人体自燃”的案例,实际上是谋杀案。
既然对这些案例的记载都相当清楚,而火源又总可以找得到,还有什么神秘之处?在很长时间内让人迷惑不解的是这些死者为什么会被烧得那么彻底。人体大约80%是水,是很难独立燃烧的。这是那些试图焚尸灭迹的凶手要面临的难题,如果不添加足够的燃料,他们很难将尸体焚毁,更难以将之烧成灰烬。只有在很极端的条件下尸体才能被烧成灰,例如在火葬炉中。但火葬炉的温度要比住宅火灾高得多,而且在那样的条件下,尸体的焚毁程度是均匀的,决不会还有一部分保存完好。“人体自燃”虽然总能找到火源,但这类火源都是香烟、蜡烛之类的小火,令人难以想象为何会有那么大的摧毁能力。即使是星火酿成巨火,把整幢楼都烧毁,尸体也不会被烧成灰烬,总是能发现烧焦的骨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966年发生于美国宾州的一起“人体自燃”现场,死者只剩一只脚。)
在19世纪,那些主张人体能自燃的人认为这跟酗酒有关。他们注意到,大多数死者在死前都大量饮酒,因此他们认为酒精在体内组织堆积,能增加人体的可燃性。有的人还主张酒精在体内分解后,产生了氢气或其他可燃气体,遇到一点火花就可能导致爆炸。生物化学的研究否认了酒精能在体内产生可燃气体的说法。即使大量饮酒,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也不足以对人体组织的可燃性产生任何影响,在血液酒精浓度能达到影响可燃性之前,酗酒者早已中毒身亡。在一项实验中,一只老鼠被在酒精中浸泡了一年之后点燃,其皮肤和表层肌肉都被烧毁,但是内部组织和内脏并未受影响。对博物馆中那些在酒精中浸泡的时间更长的动物标本所做的实验,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不可否认,酗酒的确与“人体自燃”有关,但这并不是因为酒精能增加人体可燃性,而是因为人在酒醉后,对火源不小心,被点燃后也不感到疼痛,不会惨叫或喊救命。
还有人提出了种种奇谈怪论试图解释人体自燃,例如说人体肠道内充满可燃的气体、人体组织内含有磷之类的可自燃的化学元素、体内核物质发生大爆炸、外星人发射死光、类似于“气”的体内神秘能量的爆发甚至是由于“怒火中烧”(美国著名小报《世界新闻周刊》在1986年11月18日曾报道有一位旧金山的传教士在布道时,由于怒气冲天,炸得粉身碎骨。《世界新闻周刊》上的所谓新闻基本上是捏造出来逗人一笑的,国内有的报纸不知此中奥妙,经常正儿八经地转载它的报道),这些说法,就跟田维顺、毛法根的说法一样,都属于凭空设想的无稽之谈,不值一驳。只有两种解释有些科学依据,值得考虑。一种认为“人体自燃”是静电引起的。人体能够产生几千伏的静电,某些人甚至能高达3万伏。这些静电通过毛发放掉,在正常环境中是无害的,但是在某些极端的环境中,比如在周围充满可燃物质的工地,人体静电放电可能导致爆炸。不过,这类爆炸虽然发生过多起,却没有一起是像“人体自燃”那样,人体被炸得粉碎,而房间、家具的受损程度却很小。另一种解释是说“人体自燃”的受害者是被球状闪电击中的。这也从来没有被目击过。
既然在“人体自燃”案例中,调查人员总能找到火源,又何必求助于像人体静电放电、球状闪电这类无法证实的新火源?问题是,像烟火、烛火那样小的火源,如何能把人烧得粉身碎骨?目前学术界较为公认的一种解释是“灯芯效应”(也称做“蜡烛效应”)。这个解释在大约100年前就已被提出,现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证据的支持。根据这个理论,酒醉或昏睡中的人穿的衣服被火点燃,皮肤被烧脱落,皮下脂肪融化、流出,衣服被液化脂肪浸湿后成了“灯芯”,而体内的脂肪就像是“蜡”,源源不断地提供燃烧的燃料,于是尸体就像蜡烛一样慢慢地燃烧,直到所有的脂肪组织都被烧完。这个理论可以解释上面所归纳的“人体自燃”的特征。妇女和身材肥胖的人体内脂肪含量高,因此容易成为“人体自燃”的牺牲品。多余的脂肪通常储存于躯干和大腿,因此这些部分的烧毁程度最严重。没有衣服覆盖的身体部分不会被烧毁,因为融化的脂肪需要有衣服做“灯芯”才能充分地燃烧,但是液化脂肪流到这部分的身体后,会将那里的皮肤烫伤,而死者残存的身体部分的皮肤的确有烫伤的症状。脂肪燃烧时会产生浓烟,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死者房间的天花板和墙壁会被熏黑。有些融化的脂肪会流出体内,流到地板上,由于没有衣服做灯芯,它们不会燃烧,而残留下来,这就是为什么在死者身下的地板总能发现黄色的粘稠物质。
1998年4月,加州犯罪学学院的约翰·德·哈安(John De
Hann)博士做了一个实验首次验证“灯芯效应”。他从屠宰场买了一头死猪(猪的脂肪含量与人体相当)裹上毛毯,放进一个模拟房间中,房间里有一个木架,上面放着一台电视机。他往毛毯上浇上少量的汽油后将之点燃。猪油流出后浸泡毛毯,使之成了灯芯,火焰便以猪油为燃料持续燃烧了7个小时。大约5小时后,猪骨头被烧裂,流出了骨髓,骨髓大约含有80%的脂肪,因此继续燃烧,直到把骨头烧成了灰烬,甚至比火葬炉烧得还要彻底(火葬炉焚烧后,还会残留一些骨头)。而猪身体没有脂肪的部分,像脚的下部,则保存完整。周围的家具都没有着火,只有电视机受热融化了。这一结果与所谓的“人体自燃”完全相同。星火可以燎身,一点小火的确可以把人烧得粉身碎骨,并无神秘之处。
2001.9.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