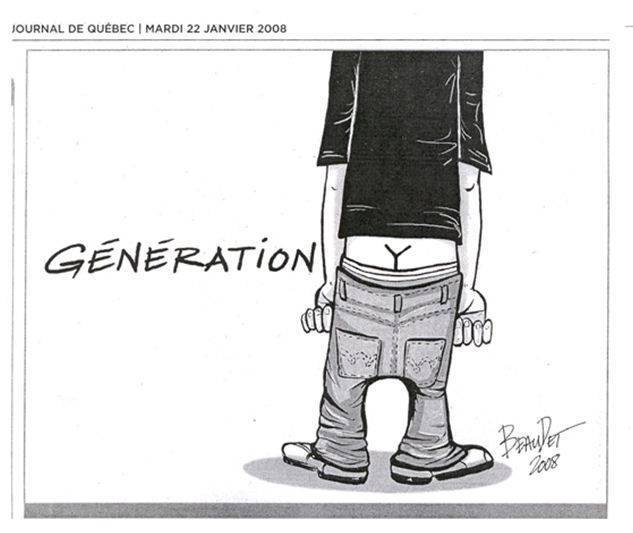我见工的时候,老板问:“你对Team Work怎么看?”
我大大咧咧地说:“Team Work跟结婚差不多。象我念MBA的时候,有十门必修课,都是学校安排的team,不许换组员,这就象包办婚姻,而且禁止离婚。有的team每个人都恨死了别人,找学校理论,学校说,这是给你们创造一个实际工作的环境。有人不服气,说,工作时我是拿钱的,看在钱的份上,忍就忍了,可现在我是交钱的,三千美刀一门课,十门就是三万,为什么要把我跟不喜欢的人绑在一起?学校说,fine,不喜欢你可以退学。选修课时就好了,可以自己组对,这叫自由恋爱。我想工作中的team,应该是包办婚姻,不过,好在可以离婚。”
两个老板乐得哈哈地笑,第二天给了我offer。
说实话,我包办婚姻还算不错,但是我们还是喜欢自由恋爱,到选修课时,大家一声欢呼,大叫:离婚了!再也别来找我!我们象出笼的小鸟一样,自由恋爱去了。
我的自由恋爱的第一个婚姻,精挑细捡了半天,最后选中了小W,小艾,王非。四个中国人,我们一起学企业金融。这门课很重计算,中国人毕竟数学好。
小艾是比利时来的交换学生,单身的北京女孩儿,如果硬要把她算作我校学生的话,她是我校最出色的学生,仅仅在美国呆了三个月,就拿到一个十四万的offer。她才二十六岁。
王非是香港来的青年才俊,也是二十六岁,在香港金融界厮混多年,已是CFA三级。王非极度可爱,不管老的小的,都喜欢他。有一次我把一个老乡带到同学聚会上,老乡散会了对我说:我相中了王非作女婿,你能不能帮忙?
小W新婚,一脸的甜蜜,她长得一副纯情,身高一米六五,着零号服装,34D。我一个女人,第一次见到小W时也有点失态,呆看了她半天,终于还是没有忍住往34D瞄了几眼。王非是个拽人,当时已稳坐了我校男校花之位一年有余,从来不说哪个女孩子漂亮,见到小W也是晚节不保。我们开完第一次会,王非在我耳边嘀嘀咕咕:“小W真漂亮,可是,这么娇滴滴的样子,怎么能念MBA?小艾也好,典型的女强人。” 我想最好的总是留在最后才评,就无限期待地等他说下文,等了两分钟,没有等到,就很不高兴地问:“那我呢?” 王非一脸鬼笑:“你跟她们不同,你是另类作家,猩猩人类。”
我脱下跟象针尖一样的高跟鞋,在学校的走廊里追着王非打。
自由恋爱就是好,我们四个很开心。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这个爱好使我们四个人永远很穷,因为,不论是纯情少妇也好,女强人也好,青年才俊也好,另类作家也好,我们都是购物狂。
每当作业做到很累的时候,小W一个手机,就call来了W先生,全当是我们的司机,四个人钻到车里,开去mall里疯狂采购一番,真是爽呆了。你不能想象,这里买的最多的人是青年才俊王非。王非的行头可真多,光领带就有百来条吧。
三个女生,身材相差不多,全部是零号,衣服可以混穿,小W最大方,常常叫我和小艾穿她的衣服。
小W是本校校花。校花与我和小艾这样平常百姓的不同在于,校花有34D,我们是飞机场。
校花的衣服很暴露,每件都暴露无疑她的34D,她拿了这些衣服来给我和小艾穿,我和小艾互望一眼,异口同声说:“我们不穿!”
校花是学文科的,搞不清楚数字,我有次发现她把我们算的账少打了三个零,从此我们不再相信她。不过这无伤大雅,我们三个算起数字来都是刷刷地,文科的可以负责一些文字工作。
有时候组里同时有一个男校花和一个女校花,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因为,常常有人来骚扰校花们。
我们学校的色狼,不管我们作业做到多么关键时刻,都会直直地闯进来,勾三搭四地说些无关紧要的废话,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小W的34D。
我们学校的花痴,最喜欢来找王非八卦,常常有人会突然进来,嗲声嗲气地问:“王非呀,我上次忘记问了,xxx卖吗?多少钱?”
我说:“你去死了,问点有创造性的好不好,xxx怎么会卖?她都可以买了。”
香港明星,从一线到三线的价钱,王非如数家珍。
我说:“王非,你太过分了,一个男孩子,怎么如此八卦?”
王非比窦娥还冤:“我妈跟我说,我爸跟我说,我同事跟我说,我怎么办?有一次,我同事炒股赚了钱,说请他爸去吃一顿,我问他到哪家馆子吃,人家笑死了,说是吃一个三线的,五千港币。”
在两位校花被骚扰的时候,两个飞机场默默无闻地把作业做了。
股市持续大跌,工作找不到,除了小艾以外,我们连一个interview都没有。刚进校的时候,是2000年,看了学校的广告,毕业生找到工作概率99.8%,平均工资十一万,所以我们都是按那个标准计划将来的生活的,现在找到工作概率20%,平均工资六万。对我们这些80%们来讲,平均工资是零。我们存的钱见底,就快穷疯了。
有一天我和小艾被追花族吵得不胜其烦,受香港明星启发,对那两朵花说:“不如你们俩也卖吧,我们两个负责收钱,分点红,也好买几件漂亮衣服。”
于是我和小艾,用Excel啪啪啪地打出一堆价钱:看女校花敏感部位一眼50块,问男校花一个问题20块;摸女腿一下500块,男腿一下300块……
最后我问:过夜怎么算?
王非尖叫:“打死也不过夜!”
小W大大方方地说:“过夜1000亿。”
我们瞪大了眼:这文科女人搞不清数字,她知道一千亿是多少钱吗?
我小声地问:“美金还是里拉?”
她大声地说:“美金了,要里拉到哪里去买衣服?”
我说:“小姐,现实一点,比尔盖茨脱了裤子当当,才当得出九百亿。”
她理直气壮地说:“他信用好不好?好的话不是还可以贷款一百亿。”
我说:“好好,一千亿就一千亿。”
小艾说:“这也贵得太离谱了吧。”
小W的价钱,因为她自己常常把零搞错,浮动很大,可以上下几千倍。今天一千亿,明天10亿,后天又变了,连她自己也搞不清楚。正好我同时在选保尔的国际金融,就拿她的价钱到另一个自由恋爱的组里练习一下外汇兑换。
有一天,讲到一个香港明星,是小W的偶像,说价钱是港币三十万一夜。
小W黯然神伤。我们趁机说:“你要不要也调下价?”
小W大概是伤心过度,竟然随口说:“那我就卖100万吧。”
我们一算,乖乖,这下差了十万倍。
快毕业了,我们还是没有工作,王非说:“惨了,钱用完了,我一亿也卖了。”
小W看有人陪卖,兴奋地问:“那我是卖多少钱的来着?”
我说:“你原价一千亿,上次降到100万,不过,忘了问你,是100万港币还是美金?你偶像的价钱是港币。”
黎柳蝉
October 9, 2003 11:32 PM,一稿
November 1, 2003,二稿
《新世界时报》2009年6月19日,36版